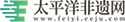编者的话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语出《诗经·小雅·伐木》,意为鸟儿在嘤嘤地鸣叫,寻求同伴的应声,比喻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我省作家、评论家马钧的新作《嘤鸣友声:致李万华书简》是一部关于近年来活跃于散文界的青海作家李万华散文创作的专论。书中,马钧以中国式的品评方式,以书简的形式,构筑了一种崭新的评论模式。
本期“江河源”副刊特推出我国著名翻译家、诗人树才和程一身对本书的推荐语以及我省作家、评论家马海轶和郭建强的评论文章,带领读者走进马钧的文学语境与评论世界。
《嘤鸣友声:致李万华书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名家推荐语
马钧这本书结构形式很奇特,有独创之处。李万华是在自由、安宁的隐退状态中用心写作,草木含情、语言简洁。马钧是一位学养深厚、见解深刻的学者型作家,比李万华年长,却对她创作的散文格外欣赏。我认为,是一颗推崇和珍惜之心推动他,以书信体的形式,写下这些灵动的诗性评论文字。这也是两位作家的心灵之间的互动和互鉴。
——翻译家、诗人 树才
马钧此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文体融汇的出色实践,更在于对科技异化人性潮流的反动。科技在给人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人沦为机器或手机控,从而阻碍或锐减了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交流。马钧在其系列新作中着力激活对话与书信这些深度精神交流方式,灵活兼容、真诚亲切,有助于维护或张扬科技时代的健全人性。
——翻译家、批评家、诗人 程一身
历尽艰辛仍觉不虚此行
马海轶
李万华是我们此间颇有成就的作家之一。我的老朋友马钧兄看好她,给她作评论,竟一发不可收拾,洋洋洒洒写下去,直写成一本数万字的书。现在这本书要出版面世,老朋友嘱我看看,我点开书稿文档,单看目次,就把我吓住了:我从未见过如此新颖别致的目录形式,也从未见过如此涉猎广泛、汹涌澎湃的博引旁征。据说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是一部打通古今中外诗心文心、又不能被归入任何学术体例的奇书。我倒是早就慕名买了,但人贵有自知之明,一直没有勇气仔细研读,搁在书架的最上层。我知道马钧兄是钱先生的拥趸,长久以来研究钱锺书而且深有心得,对钱先生推崇备至,我想,《嘤鸣友声:致李万华书简》应是致敬《管锥编》之作。
我努力地读下去,就像攀登一座插入云峰的高山。虽然气喘吁吁,精疲力竭,却看到了奇特而美丽的风景。我看到了灵感的光华处处闪现。这部书的结构和立意多是创造性思维瞬间突发的产物,奇峰突兀,天外飞来,不免让我们这些思维平庸的人拍案惊奇;我也看到了知识海洋的广阔浩淼。本雅明曾经说过,用引言可以写成一本书。要统计马钧兄在此书中引用的语录、人物、流派和著作,这是非常困难的作业。
“我像乡下的媳妇用许多色调不一的碎布缝制出好看的布包一样,我以我的目光,飞针走线地缀补一篇篇你的文字,我便在某日,一下子就获得了一种直觉性的确定感——到目前为止,我所能搜罗到的、有关你的所有文字给予我的一团阅读印象。稍作概括,姑且名之曰古灵精怪。”整部书稿由十篇构成,以“古、灵、精、怪”为关键词。在“古”与“灵”之间,还论述了李万华散文的“诗”性,散文的“文”性,以及“笔记性”“随笔性”。勾勒和梳理了李万华创作中的“原生性精神资源”。“四气”论述当然是整篇论文的主干,其中以“灵气”最为精短,计4500字。本篇中先后被“引用”的人物有刘勰(《文心雕龙》)、卡尔维诺、钟嵘、庄子(《庄子·田子方》)、袁中道(《心律》)、钱锺书(《围城》人物赵辛楣、方鸿渐)、阿尔伯特·吉尔吉(雕塑作品《忧郁》)、钱锺书(《宋词选注》)、维科、彼得·潘。仲尼、杨万里、安德烈·波切利是被引用者引出的人物。马钧从刘勰引起,迅速“兑换”成卡尔维诺,没有任何过渡,钟嵘和庄子就站在我们身后。孔子“目击而道存”的话音未落,印度因明学和佛学概念便登堂入室,还有一把日本人翻译的梯子立在我们无法预料的墙角。接着到来的是《易经》《焦氏易林》和青海人舌尖上的方言俗语。人物和典籍之间切换自如,打通了时间和地域的隔墙,他们就像是等在某个路口,随时听从评论家穿越时空的召唤。大量、紧密的引用,聚焦于李万华的第二个品相“灵气”,最终形成“灵气”同样属于“文学的一种价值、一种特质和品格”这样的论断。在密集的引用形成的逻辑链条中,评论家不时插入形象生动的点评和概括,譬如:“你的这些造句和比喻,从来不使用现成的、旧有的表达,用旧的比喻、用旧的造句,就像火柴盒擦皮被火柴头擦秃了,就擦不出火了。你是时时更新你的语言的擦皮,以保证随时随地的闪念都能擦出闪亮的火花,匪夷所思的火花,而不是仅仅擦出一股火柴头上的硫烟。”多年前,我在马钧兄一组题为《芸窗碎锦》的随笔写道:“意象迭出、气象万千,在关于日常生活漫不经心的叙述之下,重新审视了逻辑与观念的秩序。看似随意,实际上用心深、用意奇、用词绝。在他独门所创的意境之下,生活、语词、时代都不过是材料而已。”这些特质在这篇论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张扬。
“在文学批评中,应当推崇公正典范、努力保持独立而自由的批评者尊严”。这是马钧兄曾给我的一篇评论的编前语中的一句,当为中肯、恳切之言。读马钧兄多年,品马钧兄多年,除了作为铺垫、说明、印证的“引用”部分,如果要勾勒出他的文学评论的轮廓和范式,大致由三部分构成。从理清或曲折,或复杂,或潜伏的情节开始,以全视角的文化镜头扫描,使用技术和经验的手术刀,解剖、解析、评价这些文字和情节,给我们提供读懂它的可能。接着分析上述的情节,挖掘它们包含的独特的思想或哲学,然后用一定的价值系统匡正评价这些思想。最后,将分析评价的作者和作品置于更广阔的艺术进步的历程中,估价其所发挥或即将发挥的作用。马钧兄幽微烛照,处心积虑,在文学研究中,已然建立一套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机制,让读者透过他的评论,从文字的“表象”看到“内脏”,从情节的“血液”看到“经络”,从思想的“骨骼”看到“肌理”。“她以微观的幽深、繁密、娴雅、隐秘,缔造世界的精微与生机,缔造世界的曲径分岔,缔造世界的殊途同归。”李万华的创作如是,马钧兄的文学评论亦复如是。
书简写到李万华《焰火息壤·柳湾彩陶》时,马钧兄说:“但你已经把自己深深浸入到那些文物里,以沉浸式的体验,像巫者一般,穿越于远去的时空。你的‘仙家法术’既不玄虚,也不神秘,你最为拿手的功夫,恰恰是为玄虚、神秘、古奥的知识祛魅。方法就是启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唤醒早年的记忆。你不用小心地求证,你只知道大着胆子去利用自己的经验、记忆去合理想象,去进行一次次文学化的情景再现。”读到此,我更想知道像他这样渊博而率性的评论家,在这种偏于严肃和严谨的文种中,会不会、有没有启动自己的生活经验,以改变文本整体的氛围?果然,在论述到《丙申年》结尾的文脉和词气时,他笔锋一转:“结合整个文章,尤其是最末一段的语境,再细细品味一下,恕我直言,你的这个古今语境的混搭,还真有些‘穿帮’。转换一下我的意思,这文末的‘词’,如同新植的牙齿,它再怎么按照原本的模样嵌在空缺的地方,它也会因为没有经过恰切而周到的磨合,多多少少让舌头和咬合肌感到一些异样和不自在……”这不再是一本正经引经据典的马钧,而是牙痛的马钧,趣味的马钧,随心所欲的马钧,浮想联翩的马钧。看起来,他新植的牙齿有点水土不服。他想,要把它写到文章里,于是,就将它写到文章里。
李万华在《金色河谷·回声》中写到缠线的技艺:“爷爷的手并不灵巧,但是捻出来的毛线匀细而有弹性。我缠线团渐渐得出技巧,如果线团绕得过紧,毛线会失去弹性,我便以手做轴心,给线团留下空隙,这样绕出来的毛线团又柔软又蓬松。”马钧兄在任何“松散、宽舒,富有张力和弹性”的地方,都可以做“切口”,以期求得“不相关地相关着”。果然不出意料,他将“缠线法”蝶变为“文字章法”:“这岂止是在缠线。这里你所呈现的缠法,完全适用于文章这种织体。文章的起承转合,不也同样需要时时给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意义留下‘空隙’,既不能绕得过紧,也不能绕得过松,松紧之间要保持‘又柔软又蓬松’的弹性。”如果到此结束,就不是我们熟知的马钧。他快速“切换”:“只保留文脉的内在指向和趋向,是书法上的笔断意连——我忽然发现我们书法的布局节奏,行笔走势,完全是笔记性的随性随意。”
当年蔡元培先生说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由此推测,大学者也应该如此。马钧兄熟谙典籍,信手拈来,惊人的学识直将这部书累积成百科全书,他庶几符合大学者的定义了。我还看到了想象的层出不穷、语言的缤纷多彩和行文的纵横阖捭,这些瑰丽的景象,在本来比较枯燥的文学评论里稀罕看到。凡此种种,都让我有历尽艰辛仍不虚此行的感觉。艺高人胆大。没有灵感、渊博和想象,没有对语言的深刻洞察和娴熟驾驭,就不可能有丰沛的创作动力,也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包罗万象的书。不仅于此,马钧兄还说:“我肚子里还真垫了几根大梁般的‘理论支持’”。正是文学和美学的理论大梁,撑起了这部内容庞杂、结构繁复之书的圆顶。我想,这部书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初衷。马钧兄说,“秘密炼制时代的稀有物质,在精神的作坊聚集心光,织就心锦”,与其说这是对李万华作品的评论,无如说是夫子自道。他用“古灵精怪”概括李万华的文学特征,而马钧兄这部书的精神气质也与此完全一致。朋友们只要开卷阅读,方知我所言非虚。
我还记得小学教室墙上挂着的爱迪生的名言:“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我也相信这句话揭橥的真理。作为马钧兄多年的朋友,我可以证明,他在这部书里表现的才华,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异禀,而是许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马钧兄推崇“万人如海一身藏”,热爱《归园田居》,喜欢“默存”,熟悉青海文坛的系列“隐身人”,从中不难看出他的人生哲学和价值取向。在一个众语喧哗、甚嚣尘上的时代里,马钧兄一如他反复提到的齐奥朗:退回孤独,远离名利场,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写作,兼收并蓄各派思潮和学说,努力探索人生的真谛。他向往这种逆着“世风”的生活,而且把理想变成了现实,他努力的栽培和浇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是幸运和幸福之人。
在郊野沉吟试听流连万象
郭建强
马钧的很多文字,很像是郊野的刻石画像——首先是文化和文明的孕生物,有着铭文勒石的质感和品相,细究,却又觉得与郑重的路标和指示牌存在巨大的差异。怎么说呢?他的文字和文学的趣味因着郊野的自在和沉着,而将书斋隔窗听雨呈现出“修竹齐高树”的自然的状态来。
马钧曾舌耕大学课堂,现为省报文艺板块的执掌者。以上仅仅是铺垫,马钧更是一位秉烛夜游、谈龙说虎的慧心人,是以多种艺术形态和生活材质得取诗魂光焰,并且尽一己之力将诗之明亮和邃远传播于四方的“养蜂人”。其实,他还是一位偶尔使用分行,在更多时候以非诗的形状豁显诗核的诗人。
这样的诗人,往往沉溺于他人难以猜度的欢乐,蹀躞于郊野,以获得天光水色隐秘的激荡。马钧的文学志向,趣味,形制,很早就显露出郊野独行沉吟昏晓的“体气”。十年前,马钧出一册文学评论和艺术品评的论著,名曰 《文学的郊野》。他的执拗与绵厚、清简和肥腴,于这本书中有着令人深刻的表现。可以想见,似如马钧般的握管者,其乐独有;更多的时候,朋友们也未免替他可惜——大雅几人听?
机缘就这样来了。青海作家李万华的锦绣文章的文气、文采,激引马钧先生共赏雕龙文心,同探诗艺构理。我读“马氏文通”别册——《嘤鸣友声:致李万华书简》,直有从聆听独乐而观对舞的感受。而此书编舞超然,种类混搭,舞步多变,却又脉流清楚,是跨越了批评和文论的边界,在随笔的原野驰息的灵兔和回归的野马的自在展演。被马钧以“精灵古怪”为线路细品慢鉴的李万华,反映出论者其实是另一种相征的“精灵古怪”。论者与被论者的相互激荡(更多的是李万华对于马钧的激荡),引申出审美“手谈”的意蕴、美感和互嵌。这是一次稀见的双向挑选,其手语、舞姿、意态,莫不因为重华繁绽而格外“酷飒”。这样的书写,基于论家和作家的同情共感,恰如两人行于暮色郊野的灵息互通;而郊野也在这样的吸引、辨识、欣赏中,从个体中复活,展示出颅顶天空的浩瀚和身边万有的生动。
我之所以用比喻表达马钧文章的特质,以及对于李万华的辨认(马钧于此明白地判断“李万华已是青海作家中的翘楚,在全国优秀作家中也是星辉难掩”),是因为“比兴”从来是汉文化表达方法和认知事理的核心。在此,马钧通过比较,选择了年幼于他十多岁的李万华;随之而引譬连类,兴致勃勃,舌灿万华。读其文,马钧借李万华的文章腾挪翻转,速览静品,从文华诗心而文统革新,从风土地理而个人经验,乃至在更为宏阔的空间代言指导,调息运气,织就了多材质、多技法的立体长卷堆绣。换句话说,马钧借与李万华的深研细赏,又一次完成了自我“分身术”——是一个马钧与另外一位或者多位马钧的“辩经”、问难和会心一笑。然而,《嘤鸣友声:致李万华书简》生起又绝非是马钧独舞。在笔纵墨涌之际,李万华的文章如同药引,如同铜镜,是酵酿马钧从新的路径再做郊野之游的光影。《西游记》第一回中便说道:“料应必遇知音者,读破源流万法通。”马钧遇李万华,真有读破源流通万法的意思呢。
于是,我们看到马钧不仅屏息于李万华的精神气质,瞩目于作家美质的构画气韵,甚至像个从《隋唐演义》《大明英烈传》中走出的通阴阳五行,知易理之变的堪舆先生,连作家的名字也作为暗通审美的密码,而置设于天象人文考度一番。看上去,这种烛微探幽近乎于癖,实则是将李马二位的文字都显影于汉文化的深广背景中,复活那些几近于弃、几近于忘、几近于不能的感受和表达力。于是天象气候,地理草木,风卷云舒,书册管弦,影碟唱机,往事近影,纷至沓来,与心境笔意,枝节勾缠,蓬生蔓衍,历时共时,重绘人文,形成了李文马说的奇观。这双重的文心诗眼,在阔大而活跃的传统巨流的衬映下,同时展现出视野的宽度和体察的深度。这种书写的宽博深远,暗合、并且也在改写着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判断:“历史记述已经发生的事,而诗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在今天,史与诗的互融,情与境的同构,已经成为各式艺术表达的常见;但是,所表达的形制和指向,仍然清晰地成为二者泾渭的分界。如何跨界、越界、调取花粉丰富味道独具的文学之蜜、艺术之蜜,马钧在摩赏李万华的文辞中,透露出了一些秘密的信息。在我看来,马李二人都是熟谙将可能之事写作历史,或者将历史写作化为诗性可能之事的圣手——这里的历史,因为是特指个人的际遇、经历和经验,而在一种可逆的观望中,生成了类似崖石胞苔,珠串包浆的质感和光泽来。如此,马钧论李之堆叠、回旋、类聚,可称为是辐辏的探寻和兴叹。只是,马钧的“美的历程”,是偏好于时空的过渡地带——于地理来说是郊野,于时候来看是晨昏。正是在交接换替的所在,一个人、一个人的踪迹印痕,才于难显之处标明得清晰。马钧喜悦于天光将明或者暮色苍苍,这时候,他的神思灵感最为充沛,他的语言的成色最为醇厚。《嘤鸣友声:致李万华书简》分为十章,其中四章写于卯时,亥时写出三章,辰时两章,酉时一章。此中既有生活和工作的限阈,又何尝不是生物钟神秘的设定呢?马钧也出色地把握了时机,在这个为尼采、波德莱尔、克尔凯郭尔、鲁迅等先贤钟爱的“一天的郊野”,他让自己的文章如同晨光晚照的景象,呈现出别样的色彩。相应的一种情况是,很多美妙的艺术品并不适合在强光下欣赏,倒是在有几分沉着的光线下,反而能够焕发出饱满而灵动的声响。马钧之于李万华文章的注视、倾听和理解,恰如在郊野的舞台上,两个灵魂的遇合、交流和酬唱。其间,主体观念、情思模式、场所感知,移形换位,颇有“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的感发和感动。我以为,这个再阐发、再塑造的过程,接续了中国早期文学“诗意创造冲动的流露,其敏感的意味,从本源、性格和涵蕴上看来都是抒情的”(见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的脉流,而马钧的文思情理并织,宏微共举,物我同在,既是对于李万华知音弦动,也是作品与评论、文本与本文的文学激荡。他,他们穿行于昏晓的目光、步履、行姿,本然地带有几分孤独的味道,可也是这几分寂寞,愈加显示出沉思之美的珍贵和耀目。台静农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论及杜牧诗时准确地写出这种认识:“……而寂寞当时,其磊落抑郁之怀,不觉地流露出来,寓呜咽豪放,寄清峻为秾丽,往往令读者低徊感激,有不尽言外之意……”
我是在“低徊感激”中,几次体会那“不尽言外之意的”。我从马钧的文章中,读出了新鲜而苍远的李万华,也读出了一个文学烛照者的形象。回到拙文初始,马钧的社会和精神的多重身份,似乎是他以浓度极高的情感认同、审美认同,与李万华对谈共舞的动能之一。我是说,在这里存有一位作家对于另一位作家坦荡欣赏的美好品质。实际上,在青海有很多作家得到过马钧诚挚的邀约,并在“马氏文通”的视角下获得超越知识和技艺的鼓励。我也是得到过马钧惠赐心香的朋友之一。
20世纪80年代初,瑞士文学批评家让·斯塔罗宾斯基先生,在接受法国《文学杂志》的访问时,提到了他的前辈、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在1922年写下的六篇文学批评。这几篇文章是由蒂博代的讲演而来,斯塔罗宾斯基重提60年前已如郊野松柏的文论,是因为蒂博代关于“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的划分和阐释,学理功能仍然强盛。马钧的职业和修养可以说是三者俱占,而他创造的热情、越界的能力,则倾向于大师批评中的“审美的批评”。这样的批评要求作者涵葆对于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既是批评的分析,也是审美的创造。落实到调弦定音,则有“既不以法缚,亦不以法脱”的品相。实际上,这就是斯塔罗宾斯基所期望的,在三种批评上混生的更具生命力的样态。这位瑞士的教授,将这样的批评称为“随笔”。
“熟悉天性,热爱天性,尊重天性,由此产生一种热情,此乃寻美批评之真正的必要性”。这句话是蒂博代讲给批评家的。我们将之理解为讲给作家,甚至是所有人听的,又有什么不适合呢?
“建强,如啄木之鸟,开始剥啄有声吧。”这是十年前马钧赐《文学的郊野》时写给我的赠语,现在我把它转赠于读者。且随马钧、李万华行走郊野,流连万象沉吟视听,感受啄木之鸟再次剥啄有声,做出一次珍贵的美的巡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