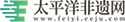■许海桅 山东艺术学院
晚明时期,阳明心学的盛行使主体个性得到解放,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董其昌也不例外。他极其信奉心学,除了有时代大潮的影响外,还与阳明后学李贽等人的交往有关。董其昌的思想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一生在儒禅之间来回转换。他年轻时非常迷恋狂禅之风,以至被人视为“狂生”,但在其出仕后,思想渐趋中庸,这不得不说是为现实所局限。身处于这样的时代,董其昌思想中的激进部分被一点点唤起,他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及袁伯修见李卓吾后,自谓大彻。……余重举前义,伯修犹溟滓余言也。”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从文中可见,董其昌对程朱理学的“已发”“未发”之说感到怀疑,当时他的朋友也未能说清,直到见李贽后才大彻大悟。之后,董氏在与朋友谈论中,他的见解又被朋友所推重,可见其思想已与李贽有不谋而合之处,也能说明董其昌的思想倾向。前面讲到,董其昌的思想是在儒禅之间不断转换的,他一生都游离在正统与异端之间,也正因如此,他后来才会拥有既不逾矩又具新意的艺术风格。
董其昌一生都在追求“淡”的审美境界,而他所追求的“淡”又是由“心”所展开的,这与他受庄禅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董其昌认为作画,需要以古人为师、以天地自然为师,他在画中题跋时就说:“画家以天地为师,其次以山川为师,其次以古人为师。”可见,在他看来,作画不仅要以天地与古人为师,并且以天地自然为师是大于以古人为师的。他又说:“画家以古人为师,已属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传神者必以形,形与心手相凑而相忘,神之所托也。”在这里,董其昌继续表达了以天地为师高于以古人为师的主张。从这可以看出,董其昌所说的以天地为师目的在于“传神”。
董其昌又指出,“神”是寄托于由“心手”与“形”构成的“相忘”。所谓“形”,是指天地山川间的自然外物,所谓“心手”则是创作主体的自我本心。在董其昌看来,“传神”的关键是物与我高度融合后的相互泯然,是物我泯然后再由主体本心所抒发的精神,可见董其昌在艺术上是以“心”为本,这其实与禅宗的美学思想相一致。董其昌也正是在此“心”的基础上,开始了以“淡”为美的审美追求。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而淡之玄味,必有天骨,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所可强入。”董其昌认为,诗文与书法一样,只有具备“淡”才能流传百世。并认为“淡”这一审美境界并非只靠努力练习就能达成,还需要“天骨”。那么“天骨”又指什么呢?董其昌在《魏平仲字册》跋中说:“尝见妄庸子有模仿《黄庭经》及僧家学《圣教序》、道流学赵吴兴者,皆绝肖似,转似转远,何则?俗在骨中,推之不去。”他认为那些庸俗之人学古人即使学得很像但也不好,原因是其“骨”乃俗。可见,董其昌所说的“骨”是指人的精神品格,一种气质和禀性,所以俗人所作之书便是俗书。由此可知,前面董其昌所说的“天骨”也就是人的天赋与气质、精神。因此,董其昌所追求的“淡”,是一种人格精神的体现,是一种自然性情的表达。
对于人格精神之“淡”,董其昌也有详细的论述。他在《诒美堂集序》中说:“昔刘邵《人物志》,以平淡为君德。……此皆无门无迳,质任自然,是之谓淡。”
在他看来,人最高的精神品格便是“平淡”,而这种“平淡”的精神也会体现在诗文等艺术中。他认为,不管是诸葛亮还是陶渊明的诗文,都是他们淡泊名利精神的自然流露,这种境界并非仅靠技巧与才情所能达到的,而是不假修饰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表现,这也就是董其昌所说的“淡之玄味,必有天骨”。那么,董其昌官居高位是怎么淡泊名利的呢?这其实也是现实所致。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党争严重,董其昌意识到这一情况可能会危及自身,便辞官归乡,远离名利场,潜心于丹青翰墨,也因此有了平淡自然的心态。这其实与苏轼、王维是一致的,都是看清现实后的一种旷达、一种超脱。
在求“淡”的路上,董其昌强调需要向古人大量地学习。他说:“昔年见之南都,……盖渐修顿证,非一朝夕。假令当时力能致之,不经苦心悬念,未必契真。”他认为,顿悟的发生是以渐修为前提,只有长时间地参悟古人法帖才能实现质的飞跃,达到高的境界。如何向古人学习?董其昌也有详细的说明,他说:“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也。”他又说:“余书《兰亭》皆以意背临,未尝对古刻,一似无弦琴者。”,在他看来,向古人学习,主要是取其精神,而非“耳目、手足”之逼肖,正所谓“遗貌取神也”。
虽然董其昌极为重视学习古人,但他也并非一味地拟古不变,他和徐渭一样,都是非常注重个性的。他说:“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董其昌认为向古人学习,便要仔仔细细地学习,把笔法、字法等都化为己有,这便是“合”,“脱去右军老子习气”便是“离”,也就是从古人法中脱出,进而形成自我风格。在董其昌眼中,“合”与“离”是学书者想要成功的必要过程,“合”是“离”的前提,“离”是“合”的目的,所以不能守法不变,这也是他批评赵孟頫的原因所在。
此外,在创作中,董其昌非常重视主体精神与情感的作用,也就是他自我之“心”的抒发。他曾说:“昔右军诸帖,半出于问病吊唁,从哀戚中结法,所谓泪渍老笔者,其书独垂至今。”可见,董其昌非常推崇具有真实情感的书作。他还说:“欲造极处,使精神不可磨没。所谓神品,以吾神所著故也。”在他看来,能够称之为“神品”的书法作品,皆是因为作者抒发了个人性情与主体精神,并且所有艺术都是如此。也正如他在画上的以“心”为本的美学观念,只有将主体的情感与精神自然而然地抒发在书法作品中,才能达到“平淡、天真”的境界,董其昌的“淡”也正是通过“吾书往往率意”而达成的。
根据前文所述可知,董其昌既深受正统儒学的影响,又追捧庄禅的本心自然之道,在看破现实后逐渐淡泊名利,向往平淡自然。其所追求的“平淡、天真”,其实就是他主体精神与个人情性之“真”的体现。